广告位招商电话:1352233568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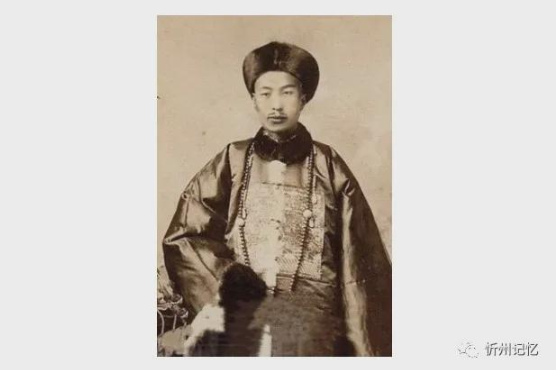
鲁潢(1727—1783),字守原,号纬纒,黎川中田(江西新城)人。国子监监生,分发山西。先后任霍州、浑源知州,摄政平定州、绛州知州。庚寅年(1770)再擢直隶忻州知州。诰授奉政大夫。
公从小气质出众,因不习惯家中烦琐事务,遂随岳父游历京城,留居北京琉璃厂。琉璃厂江西古玩商人居多,便与古字画、古董、玉石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渐善鉴别古字画、玉石,稍有积累,转为书商而身游士大夫间。与同乡陈守诚、铅山蒋士铨(文学家戏剧家)等名士交为知己。后经朋友保荐,捐授山西知州职务。
公山西居官十余年,理政辨性明决,公廉明察,政绩突出,清廉自守,敢于担当,有主见不曲意逢迎,善政尤著。对山西、忻州社会的贡献及感人事迹至今被传为美谈。
主政浑源时,一个习武之人醉酒后毁坏乡里的寺庙,乡里人把它绑起来告到公堂。公对此颇感疑惑,说:一人喝醉后怎能毁坏寺庙呢?用冷水泼面使他酒醒,问事情原委。武生低头承认详细地说了情况:自己并不是故意破坏,只是喝醉后不自知,显示一下自己的力气。公不信,让人用大砖垒起一人高的砖墙,武生用一根指头猛力一戳,砖墙从上到下出现了深深的裂痕。公感叹:这不仅是能拆屋毁庙,神力啊。为什么要酗酒逞能呢。向他讲明道理放他回去,此武生终生为有德行善之人。
主政忻州时,有一户人家公公杀死了儿媳及孙女,儿子为不扬家丑,谎称自己杀死了妻女。公对此很怀疑,审讯得知奸谋,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了公公抵命。忻州人对他敬若神明,有人还据此敷衍成小说戏剧来传颂。
公元1778年,公欲辞官归乡奉老,嘉庆帝之师---山西布政使朱文正再三挽留不能,问公:你去,谁可继任;某县令以白银八千乞求推荐;公拒绝。而推荐某州牧,理由是“其人贫而性镇静,且次不可越也。”。巡抚采纳公建议。
公要离开忻州归乡,百姓在以前为他修建的生祠前,备美酒佳肴,焚香跪在路左为他送行。与公话别的人绵延不断,依依不舍。人们又为他集资六千两白银作为回乡路费。公爽快地收下,当即将四千两作为他创立的秀容书院的运行经费,将一千两作他修建的节孝祠的祭祀费,又将一千两交养济院救助孤寡穷人(节孝祠与养济院具体缘由、位置、规模已无考)。
礼部左侍郎陈用光来山西多次,知道他事务烦多,体貌渐瘦,政绩却斐然。理政多能审理疑奇案。坏人不敢有想,隐遁或逃离。忻州历三年,地方事务渐条理,案件文书事就明显减少,社会风气明显改善,百姓安居乐业。举贤重品、重能、清廉、无私欲。其廉政、淡利、明理、世事洞明如此者稀也。赞公建树如此之大,令我们这些儒生汗颜。忻州绅士念其功绩为其立生祠。题公像所谓“九龙岗上起重馆”云云。
公理家以色养亲,扶危济困。在外宦游时,家族祭祀、田地财产,都让他侄子鲁九皋仕骥(清江西桐城派江右文学代表,人尊称为山木先生,山西夏县知县)代为打理。又为鲁佐文公家族首倡义仓,扶助贫弱。这些事在《山木居士文集》等书信中都有详细记述。回乡后,效仿汉代“万石君”扩充义仓并特别提出“收合宗族,今日惟有义田一举耳”的倡议,这在当时,是很有见地的观点,并鼎力促成了鲁陈两大氏族义仓义田的共理。公兄弟四人,他把俸禄都给兄弟们置为产业。剩余的都用于周济抚恤穷苦人。回乡后侍奉父亲鲁尚几年。公以善教化乡亲族人,以和颜悦色侍奉父母,人们都把他作为榜样效法。宗族乡里凡有事来请公决处断的,一句话没有不敬服的。五十五岁时卒于家中。
公在忻州最大的且至今使忻州人受益近250年的政绩,就是创建秀容书院。他是忻州书院的缔造者,是教育资源规模整合、质量提升的集大成者,书院的建立对忻州教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

1904年忻州历史上有名的绅士学者、画家邢尔昌绘制的《秀容文昌祠并学堂全图》
乾隆时期,清政府为了吸引人才,强化基业,改变了书院政策上时而鼓励时而抑制的摇摆态度,大力鼓励各地兴建书院,对经费困难的地方实行国家资助。并行文规定可以招聘地方上享有名望、品学兼优者担任师长,提高其薪资待遇。于是各府、州、县闻风而动,全国各地迎来了书院发展的高潮。
山西北部的忻州,幅员辽阔,自明代起就是省北大郡,民户殷繁,家有盖藏,人丰囊橐,是讴吟弦诵之声不绝于耳的晋商重镇,文化气氛浓厚。但直到乾隆四十年还没有一所州属书院,是全省10个直隶州中唯一一个没有书院的直隶州。
儒学与书院作为学校都有让人读书明理、传承知识的相同之处,也有不同之处。儒学是官学,书院以前一般是私学。儒学的教席都是官员身份或有功名的人,即儒学教授、学正、教谕、训导等各级学政官员。而书院一般是硕学大儒任山长或聘请硕学大儒讲学。儒学是培养科举人才的学校,书院也培养科举人才,但主要是创立学派,研究学术的学校。儒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国子监,下面是各府州县儒学;国子监管不了书院。儒学的学生称生员,生员指国学及州、县学规定的学生,有名额限制。书院没有名额限制,只有学舍的限制。
庚寅年(1770)年公到忻州担任知州。认为书院至今阙如,是知州的失职, 对此深以为憾 。1772年始,历三年到乾隆四十年(1775年)完成。自此始,忻州的书院成为州学。
创立书院百姓乐于接受,如久旱盼甘霖。一般而言,百姓乐于享受成果,但谋划起步甚难。对于公创办书院的这个想法,忻州绅士出于种种原因开始并不热心,但他决心已定。为表明决心,造成声势,先在文昌祠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考试,从忻州所属各县中选拔英才,延请名师讲学,全部费用则用自己的官俸承担。目的就是让州中百姓、绅士知道创办书院,事在必行,势难中止。不久,他又召集忻州知名的绅商在文庙明伦堂开会,开诚布公,说明兴建书院乃是造福桑梓的大好事,劝他们主动捐资兴办书院。到会的绅商当即拥护,踊跃认捐。又派出几位有识之士分头到各乡劝募助学,共募得捐款四千余两, 解决了建造、开办经费这个最大的困难。
州治西南最高处九龙冈源头(原名九原冈,现秀容书院),自后晋天福年间,到明代弘治年间一直是忻州儒学(也称州学)的所在地,居高临下,俯瞰全城,是堪舆学家眼中的风水宝地。但已经破败凋敝,儒学已搬回城内,且规模较小,不能满足书院的需要。公最终还是选定了这里的文昌祠旁建立书院。
在文昌祠附近择地修建书院,也是明清时期一些书院的通常做法,认为这样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其文风汇聚的地利,而且邻近学宫,便于监督管理和考课。


